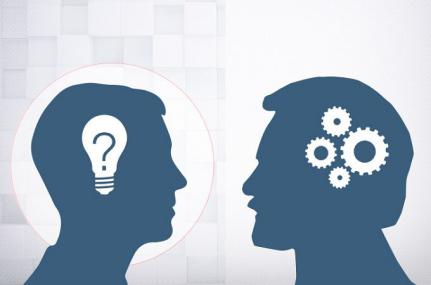人、理念、制度,這三者是一個閉合系統, 三者各自又包含了若干閉合的子系統,比如理念,即華為的核心價值觀,就包含著3句話:以客戶為中心,以奮斗者為本,長期艱苦奮斗。
這3句話也是一個閉環體。
我們必須意識到,閉合或者閉環是我們這個研究的關鍵詞,這至少反映了以下幾點:
第一,華為30多年的管理具有“形而上”的哲學性、系統性,雖然它也經歷了盲打盲試的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但從頭至今始終有頂層設計的影子。
第二,實驗性。
觀念的實驗,比如核心價值觀塑型、完型的過程長達近20年,這是一步步地反復實驗、實踐的20年,而非秀才們拍腦袋拍出的靈感。制度的實驗更是比比皆是。
何謂觀念或制度實驗?具有“假定—試錯—閉環—可檢驗—可重復”這5個遞進的過程,并構成一個完整的鏈條,方之謂也。
第三,理想主義追求。
所謂閉環即是完美,即帶有了阿Q 的“精神勝利法”的意味。阿Q臨死都在執念于“媽媽的,怎么畫不圓呢”, 所有的理想主義者身上莫不有點阿Q 的影子。
固然,任正非反對完美主義,但在理念與制度設計層面進行不斷地微調、修正、糾偏的反復實驗的過程,其實就是在力求逼近完美、逼近閉環。
當然,正如所有的思想家、建筑設計師一樣,他們都有點烏托邦情懷,但當轉身為實踐家的時候,他們面對的永遠是制度永無完美,人性充滿缺陷。阿Q永遠畫不圓那個謎一樣的圈。
這就是我們接著要討論的話題——人的異化與制度變異。
任何組織都希望自身在理念、制度、人這三方面做到最好,讓這三者能夠閉環,但沒有任何組織能夠做得到。
華為過去30多年之所以發展得比較快速和健康,是因為這三方面做得相對好,但也不是完美無缺,事實上一是充滿了缺陷,二是在不斷地填補缺陷和戰勝缺陷,三是缺陷還在到處冒泡。
人性、制度總是在與時間賽跑。時間是所有完美設計、完美追求的殺手。
人性的復雜性與人的異化
理念、制度、人,這三者什么可以變,什么不能變,什么需要永恒堅守?
2014年,我和烏耀中教授對華為大學高研班的156位學員進行問卷調查,得到的反饋居然高度一致,所有學員都認為:核心價值觀不能變,且需要長期堅持。
他們的認知為什么具有一邊倒的共識?既說明了華為的核心價值觀傳播得很到位,也反映出他們中的每一位都是核心價值觀的受益者。
在后面的研討中,他們也列舉了一些生動鮮活的例子,以詮釋價值觀怎么促進了業務、怎么激發了人的進取精神,等等。
華為的核心價值觀是建立在對普遍人性的洞察、對商業基本常識的認知、對客戶和勞動者的基礎訴求和多元訴求的把握之上而形成的一個理念體系,事實上它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同”的真理。它是普遍常識,所以它是真理。
我曾問過任正非,怎么看待有的中小企業家一個字不改,把華為的核心價值觀變成了自己企業的價值觀。任正非答:“有什么不可以?那又不是我們的創造,我們也沒申請專利。”
很顯然,這3句話具有普適性和普世性。自新教革命以來,500年來的商業繁華、科技進步和工業發展說白了就是堅守了這一常識,今后的500年、5000年仍然只能堅守這一真理,前提是商業活動仍然存在。
那么,變的是什么?人與制度。
我們常討論人性的兩重性、兩面性:天使與魔鬼,也討論人的欲望追求的正當性與非正當性。
什么叫好的管理?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張揚人性中的光明面,讓天使翩然起舞,最大限度地扼制人性中的黑暗面,使魔鬼被降伏。
從商業管理的角度來換個說法,就是要最大程度地激發個體對財富、權力、成就感的本能或理性的訴求,同時最有效地管控個體對欲望的過度追求、無邊追求和不擇手段的追求。
所以,制度在組織管理中自然就擁有了至高的地位。
優良制度的第一屬性是解放人、激勵人,給人自由;第二屬性是管控人、約束人,使人不舒服。
制度的兩重性是一個悖論,一個統一體,即將自由置于秩序的根基上。
然而,人又充滿了變化。同一個人在某一情境下是理性人、是天使,在另一情境下卻又是沖動的魔鬼;在某一角色中是沖鋒在前的戰士,在另一角色中卻是尸位素餐的官僚。
而更值得組織領導們關注的是,時間演進帶來的人的異化——曾經的奮斗者成了腐化者,曾經的英雄成了懈怠者,曾經的改革者成了改革的絆腳石。
結合華為,我將這一異化現象進行了簡化歸類:“秀才—戰士—梟雄”,這是第一類人的成長路徑。
他們從學校一畢業就進入華為,單純而富有激情,華為用一套激進的文化和激勵的手段將他們打磨成了戰士,但由于原始積累期的制度體系薄弱,江湖色彩濃厚,他們在為組織建功立業的同時,也成了一方諸候,成了抗拒制度約束的梟雄,與華為成了“半路人”。
“秀才—戰士—英雄—懈怠者(腐化者,或懈怠與腐化并存)”,這是第二類人的成長路徑。
“秀才—戰士—梟雄—英雄—懈怠者(或腐化者,或懈怠與腐化并存)”,這是第三類人的成長路徑。
這三種類型的人都曾經是華為的貢獻者,甚至是卓越貢獻者,但走到一定階段,他們就不再有貢獻了,甚至成為企業的負資產,或發展的阻力人群,那么他們就只能挪窩或解除與組織的契約關系。
這是我從一些具體的人的變化中勾勒出的幾幅粗淺、簡單的畫像,這樣的畫像我還可以描繪出幾種,包括“秀才—戰士—英雄—領袖(科學家或專家)”這一類人。
他們是在幾十年的血與淚的奮斗中與組織共成長、共命運的一類人,是一群較少被異化的、本色的奮斗者和使命主義者。
大到國家,小至家庭和個人,都永遠面對著一個令人不安的詛咒:資源詛咒。
一窮二白、一貧如洗逼出團結奮斗,奮斗造就繁華,而繁華又帶來腐化與懈怠。
制度異化:
令人不安的宿命
制度是有品格的,它取決于企業領袖的人格特質和企業員工的群體特質。
如果企業家缺乏同理心、平等意識,認為人是可馴服的動物,這家企業的制度要義更多的就會是控制,而不是激勵。
任正非身上有很濃的英雄情結和牛仔精神,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少年時他是個孩子王,經常領著一幫孩子爬樹掏鳥窩),在掌舵華為的過往30多年中,雖然他崇尚秩序,但客觀而言,他更推崇自由精神,更喜歡打破一些束縛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的條條框框。
是被管理還是愿意被管理,任正非顯然更傾向于追求后者。
任正非這樣的選擇是對的,這既發乎于他的個性與人格特質,也順應了19萬名知識型勞動者群體的普遍特質。
知識型勞動者的欲望訴求是多元的,但他們都追求獨立人格和向往自由,渴望在一個寬松的環境中實現自我價值,越是精英人才越是如此。
正像一位華為技術專家說的,“此處不留爺自有爺去處,我絕不在一棵樹上吊死。如果我的腦袋被一堆教條禁錮死了,對我是浪費,對華為是浪費,對社會也是浪費,那我還不如離開,我有權力決定我的大腦和誰去合作”。
這樣的觀點是有代表性的,它事實上規定了華為這家科技型企業必須和必然遵從的制度設計原則:以最少的必要管控保證人的自由創造。
華為的制度建設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簡到繁、從不完善到疊床架屋的螺旋式過程。
原始積累期,華為的制度是高度自由的、無序的、混亂的,它的確帶來了華為的快速成長,也有可能將華為帶向分裂和動蕩。
矯枉過正,華為花大價錢向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公司“買觀念”“買制度”“買流程”,先是削足適履,“穿一雙美國鞋”,再結合自身情況逐步固化和優化,使華為形成了一套與西方公司幾無差別、甚至更具活力的制度體系。
我的一個形象比喻是,這套制度鏈條是A→B→C→D,秩序環節明晰,簡約有力,秩序格子之內空間寬闊,也有彈性。
但是,一旦有了制度,就有了一群制度的“造門人”和“守門人”,他們是制度設計專家,普遍擁有一種發現“人性惡”的強大直覺和洞察力,所以他們偏好于發現漏洞和堵漏洞。而且他們是被挑選出來的一群優秀的人,擁有使命感和責任感。
于是,你會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度中管控的鏈條變得越來越長,更趨完善、精細和嚴密,變成了:
A1→A2→A3→A4→B1→B2→B3→B4→C1→C2→C3→C4→D1→D2→D3→D4
這就像在遼闊的馬場豎起了無數的籠子。
野馬套上韁繩就是戰馬,戰馬在有邊界的原野奔馳,就是在秩序的軌道上沖鋒作戰。
然而,當戰馬被圈在了籠子中時,它要么掙脫離去,要么就異化成金絲鳥,花言巧語以取悅他人,唯獨不創造價值。
到此為止,良制退化成了劣制、惡制。
良制向惡制的演化具有普遍性和宿命性,這也是為什么許多曾經無比偉大的西方公司最后都百疾纏身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諾基亞,比如華為的老師IBM。
企業歷史久了,規模越來越龐大,管理貌似越來越規范,而實際上是制度中兩種力量在此消彼長,助長自由和創造的制度因子在衰減,管控的因子在急劇膨脹。
制度格子化、異型化,懲治至上取代發展第一,挑錯和不犯錯成為潛文化,冒險與創造精神被壓制,導致的結果是組織活力大幅降低。
然而,歸根結底,活力才是組織之魂、良制之魂。
2009年前后的華為,正處于這樣的制度僵化的前期,也正是在這一年,任正非對管理層發出警告:你們要眼睛盯著客戶,屁股對著老板。
華為新一輪的組織變革、制度變革開啟于2010 年,當下正處于變革的深水區。這次和今后變革的長期宗旨是:簡化管理,多打糧食。
并非題外話:
關于管理與過度管理的辨析
這兩年,有一些觀點甚為流行:管理大于經營會影響企業發展是一類,重文化、輕管理是一類。
類似觀點的文章在華為內部也引起過巨大爭議。有一位華為高管問我怎么看,我的回答是,這至少是概念上的混淆。
管理是與低效和無效經營進行斗爭的工具。企業家和企業內部的全部活動本質上都是管理活動,包括文化建設、制度建設、組織建設,最終都要落實到面向市場、面向客戶的經營活動中。
文化有好有壞,制度有良有劣,組織有強有弱,隊伍有優有差,這些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家企業經營上的成敗。
中國企業現在經營上存在的問題絕大多數不是管理大于經營,而是管理遠遠滯后于市場、滯后于經營。
許多企業在所謂的“機會窗”時代,蘿卜快了不洗泥,一味想著搶風口,幾乎把全部戰略資源都押注到外部、押注到市場的單邊突進上面。
然而,司空見慣的情形是,當歡呼聲四起時,企業內部卻危機四伏。華為早期10年所經歷的管理困境相信正在諸多中國民營企業身上重演。
對任何一家企業來說,從無管理、弱管理向管理規范化演進,都是不得不過的生死坎。
事實上,大多數中小企業不是夭折于經營,而是沒有能夠度過原始積累期的管理缺失所帶來的組織動蕩。
而一些經營了20年以上的規模性民營企業,前20年之所以僥幸活了下來,是因為普遍抓住了政策紅利,再加上創始人的運籌能力、運氣,以及稍微像樣的管理。
但20年之后的今天,這些企業包括一些明星企業大多步履維艱,前面提到的三大因素都在逐漸消失。
企業和企業家們面對的是真正比拼競爭實力的時代,而所謂競爭實力,歸根結底是管理實力。管理實力體現在:文化實力、制度實力、人才實力和領導力。
不客氣地說,大多數中國企業并不具備這樣的管理實力。
當下的現實是,過去幾十年的粗放型經營已不可持續,而不可持續的根因是管理的普遍落后、管理普遍滯后于經營。
為什么改革開放40多年了,我們在全球500強中的企業數量僅次于美國,而真正經營走向全球化的企業卻只能以個位數計?
這一問題本質上就是管理的薄弱,是管理在理念和制度層面與西方公司的巨大差距。這是我們必須要有的清醒認知。
的確,有少數企業貌似存在因為管理過度而導致陷入經營困境的情況,但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結論。
前不久,我去華為北京研究所交流,那里的負責人告訴我,研發員工晚上常加班,所長和人力資源主管經常晚上10點左右去看望大家。
我將此信息告知任正非,任正非說,“你告訴他們,要給大家送點吃的喝的,每人送一杯咖啡,罐裝咖啡也行”。我回答,他們是這么做的(似乎該所前面送了別的,沒送咖啡)。
20多年前,任正非經常晚上10點左右到華為研發辦公室, 和大家“吹牛”“畫餅”,展望未來,也會吆喝大家出去吃夜宵,或者在每個人桌上放一個漢堡和一罐可樂。也有人回憶說,老板會給大家燉一大鍋湯帶到辦公室(此說有人存疑)。
這是管理嗎?當然是。這樣的管理多點好還是少點好?當然是多點好,多多益善。
管理包含一套理念體系、制度與流程體系,同時它也是一連串的管理動作的連續體。
關鍵在于:第一,知行合一。制度忠實于理念,管理行為忠實于理念和制度。第二,理念必須是對的,制度必須是良制,管理行為必須服從于企業的價值創造,服從于激發人的主動性與創造性,服務于組織的健康發展。
我們在前面講到制度的第一屬性是激勵人、解放人,第二屬性是約束與管控。良好的管理無疑是在釋放“人性善”與約束“人性惡”兩方面達成了動態平衡。
這樣的管理具有使命性和長期性。
因為事實上,人會變,制度會自演化,良制很容易失去彈性、喪失活力。
制度的第二屬性常常會掠食第一屬性的空間,使管理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管控至上,控制成為目的本身。
這樣的管理不是所謂“管理大于經營”的問題,而是管理的扭曲和變形,是良制向劣制、惡制的異化。
管理異化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
一是制度從雙屬性大幅傾斜為以管控為主,管理者的行為模式趨于防御和保守,趨于安全第一,趨于衛生型和防衛型,無限放大人性惡的一面,花大功夫圍剿并企圖消滅一切組織病菌,而不是以解放生產力為主要指向。
二是管理流程日趨復雜嚴密。
三是大多數管理者追求過程最優,為過程負責而忽視結果導向,從“以客戶為中心”變異為“以過程為中心”。
還必須看到的是,許多企業的所謂“管理大于經營”其實是一種偽現象。
表面上管理制度疊床架屋,規章、規則一套又一套,但由于缺乏頂層設計,不愿意投入成本“買管理”,或者企業家本人自以為是,拒絕擁抱科學管理,導致企業常常左邊漏水,右側補洞,一人患病,人人吃藥,管理制度與管理行為充滿了矛盾、沖突以及盲目性和隨意性。
更要命的是,這些企業雖然有成摞的制度條文,卻沒有鮮明而系統的文化理念做統馭,所以這些制度條文只是一套亂麻式的條例、規則,一套不成體系的工具箱,這樣的管理仍然帶有濃厚的原始積累期的痕跡。
直線管理咨詢的營銷顧問認為是因為管理的落后(弱管理或亂管理)而不是“管理大于經營”造成了許多企業的困境,這才是中國企業今天普遍存在的基本現實。
至于“重文化、輕管理”的說法,顯然也混淆了文化與管理的基本概念。
文化只是管理的一部分,管理涵蓋文化。
《免責聲明:本站部分內容來源互聯網,旨在分享,如有關于作品內容、版權或其它問題請及時聯系!》